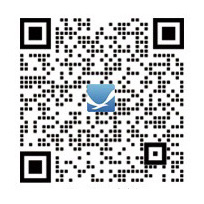摘要
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发生致使普通房屋成为“凶宅”,房屋所有权人基于房屋贬值提起的民事诉讼在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非正常死亡事件与房屋贬值间因果关系的认定、损害赔偿义务人的主观过错、“凶宅”价值贬损的范围等司法审查方面,不同判决体现出的裁判尺度和价值判断标准差异显著。本文在探讨当前已有司法案例的基础上总结其中的规律,探索“凶宅”贬值索赔民事诉讼的已有经验和审判焦点,有助于进一步厘清相关案件的审理思路,为推进“凶宅”贬值民事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审判工作提供参考,充分发挥司法在房屋所有权人权益保护方面的能动性,实现对“凶宅”贬值赔偿纠纷案件的有效处理。
关键词
凶宅 贬值损失 非正常死亡事件 财产损害
伴随国内房产交易市场蓬勃发展,因非正常死亡事件引发的“凶宅”贬值损害赔偿案件数量不断增多且问题日益突出。现行司法审判实践中就“凶宅”贬值损害赔偿案件的处理各异甚至持完全相左的立场,根源在于对“凶宅”所引发的房屋价值贬损的认识不一,针对此类案件的法律适用、法益权衡和裁判尺度长期以来并未得到系统的梳理,尤其在侵权损害赔偿法体系中定位不够清晰。“凶宅”贬值赔偿案件具有很重要的法律意义,如果司法处理不得当,将会影响到法院裁判的社会效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就会受到影响。鉴于此,笔者将结合实际司法案例对“凶宅”贬值损害赔偿进行讨论,以期为法院裁判提供些许建议,并寻求一些认知与共识。
1
“凶宅”的法律界定
对“凶宅”概念的厘定,是解决凶宅所引发的房屋价值贬损损害赔偿纠纷前提和基础。“凶宅”并非法律概念,属房屋交易市场中惯常称谓,其法律界定在我国现行立法尚不明确。“凶宅”之说自古有之,唐张《朝野金载》卷六载:“其宅中无人居。问人,云此是公主凶宅,人不敢居。”唐谷神子《博异志・苏遇》载:“长安永乐里有一凶宅,居者皆破,后无复人住,暂至亦不过宿而卒,遂至废破。”所言“凶宅”只是一个民间说法。由于缺乏准确界定的概念,当前民事诉讼中各方对凶宅的理解存在偏差。由此引发认知和后果上的混乱,有必要首先对“凶宅”从法律上作出明确的界定。
(一)司法审判实践中“凶宅”的认定
现行司法实践中各方当事人有关“凶宅”认定的主张、抗辩及审理法官的意见大相径庭,争论焦点集中于导致房屋成为“凶宅”的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具体范围。房屋所有权人主张致使房屋成为“凶宅”的事由主要有自杀事件、凶杀事件、意外死亡事件与自然死亡事件,针对房屋内发生凶杀事件、自杀事件应认定为“凶宅”理论界与实务界基本已达成共识,而对虽发生自杀但死亡地点不在房屋内的非正常死亡事件、意外死亡事件或自然死亡事件的房屋应否认定为“四宅”,司法实践中各方存在争议。
1.死亡地点不在房屋内的非正常死亡事件时的“凶宅”认定
通常情形下,各当事人对最终死亡地点在涉案房屋内的非正常死亡事件会导致房屋成为“凶宅”并无异议,但当最终死亡地点不在涉案房屋之内时,如跳楼身亡,是否仍认定房屋成为“凶宅”,目前各方观点不一。
案例1:卜某诉王某某等物权保护纠纷案
2014年12月29日,被告女儿王某某在原告房屋内跳楼自杀死亡,原告由此主张房屋构成“凶宅”并要求赔偿造成的损失,被告则主张原告基于迷信思想纠缠起诉,有悖公序良俗。法院判决:涉案房屋曾发生坠楼死亡事件,虽被告之女未在房屋内死亡,但系自房屋中跳楼身亡,该非正常死亡与涉案房屋存在较大的联系,进而影响包括原告在内的一般大众对该房屋的评价,故认定房屋构成“凶宅”。
案例2:钟某某等诉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侵权责任纠纷案
2014年10月18日,罗某某到原告家中进行维修,不慎从装修房的窗户处直接摔下到一楼地面而死亡。原告由此提起“凶宅”贬值损害赔偿。法院判决:罗某某虽是从原告的房屋内坠楼,但其死亡地点是在楼下地面,而非死在屋内,原告的房屋与传统意义上的凶宅有着本质的区别。
比较上述两个案例可以看出,虽然同为坠亡事件,但法院对该事件是否导致房屋成为“凶宅”的认定存在显著差异。案例1中,虽然被告之女未在房屋内死亡,但法院认为坠亡事件与涉案房屋之间联系紧密,会影响一般大众对该房屋的评价,而认定房屋构成“凶宅”;而案例2中,法院并未考虑坠亡事件可能引起的人们对房屋的主观评价,单纯以死亡地点非在房屋内,由此认定房屋不构成“凶宅”。笔者认为,只要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发生与涉案房屋之间有紧密联系,足以引起普通大众对于房屋的否定性评价,即使最终死亡地点并不在涉案房屋内,仍应认定涉案房屋因非正常死亡事件之发生而成为“凶宅”。
2.发生意外事件时“凶宅”认定
当房屋内发生意外事件如煤气泄露、突发火灾、意外触电、失足坠楼等情况下,此时是否应认定为“凶宅”司法实践中各方存在争议。
案例3:温某等与重庆市江北区禾田氏家柜经营部侵权责任纠纷上诉案
2014年2月25日,牟某某前往原告所有房屋安装禾田氏家经营部销售的柜子,安装过程中牟某某被倒下的衣柜砸中头部死亡。原告提起“凶宅”贬值损害赔偿之诉。法院主张涉案安装工人在温某、曹某房屋意外死亡,从民间“趋吉避凶”的风俗习惯,确存在温某、曹某对进入该房屋居住有一定心里障碍。由此肯定原告“凶宅”之主张。
案例4:程某某、王某某等与东莞市唐庭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2015年10月16日,房屋装修过程中一名装修工人在打线槽时触电死亡在程某某及王某某的新房里。2016年1月26日,原告向法院提起“凶宅”贬值损害赔偿之诉。法院判决认为:虽然房屋内发生人员非正常死亡事件未造成房屋物理受损及影响房屋的实际使用价值;但广大群众对该类房屋普遍存在忌讳、不安、恐惧等抵触心理,这又客观上导致该类房屋相对难以转让、出租或交换价值贬损,故本院认定唐庭公司装修工人的非正常死亡致使案涉房屋价值受到损害。由此肯定原告“凶宅”之主张。
通过以上两个案例分析得出,现行司法实践中有关意外死亡事件发生时“凶宅”之认定,原被告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较大争议,案例3及案例4中,原告均主张构成“凶宅“,被告均辩称“凶宅”之说属于封建迷信进而予以否定,然而,法院普遍持空前一致的肯定态度,主张基于意外事件的发生会引发人们对涉案房屋普遍的忌讳、不安、恐惧等抵触心理,对涉案房屋的居住使用产生一定心理障碍,由此认定发生意外死亡事件的房屋构成“凶宅”。笔者对法院之主张表示赞同,意外死亡事件之发生虽难以预料,但现实中人们普遍对发生意外死亡事件的房屋心存芥蒂,进而不愿居住于该类房屋内,因此,发生意外死亡事件的房屋应认定为“凶宅”。
3.自然死亡或因病死亡时“凶宅”认定
针对房屋内发生自然死亡或因病死亡事件时,房屋是否构成凶宅,司法实践中亦存在相当争议。
案例5:张某等诉上海步阳置业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2015年10月27日,原、被告签订房屋无偿使用协议,约定原告将该房屋无偿给被告使用,被告将该房屋作为其员工宿舍使用。2016年9月29日,被告一员工猝死于涉案房屋内。原告主张:该房屋内发生被告一员工猝死之非正常死亡事件,因此成为“凶宅”;被告主张:人的死亡是正常现象,房屋内死人与房屋损失之间既无直接关联也无法律依据,由此否认“凶宅”之说。法院判决主张:鉴于臧某系被告员工且系被告安排臧某居住于涉案房屋内,又臧某的死亡确有可能对涉案房屋价值等带来不利影响,故结合本案实际情况、社会价值取向及公平原则等情况,被告应给予原告一定的经济补偿。由此肯定“凶宅”之说。
案例6:刘某某与张某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上诉案
2014年7月张某某、刘某夫妇与原告签订租房协议,用于夫妻二人居住,2017年3月14日,张某某突然猝死于原告出租房内。原告刘某某主张:依据《民法总则》和公序良俗,张某某死亡后的宅院已成为“凶宅”;法院主张:生老病死乃自然现象,张某某的死亡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病亡于刘某某的宅院亦非其本人有意选择。根据医疗记录内容,张某某病发原因为自发,由此否定“凶宅”之说。
正常死亡包含两方面内容:基于年事的自然死亡和基于疾病的因病死亡,比较上述两个案例,法院对于发生正常死亡事件时“凶宅”的认定持有不同立场。在案例1中,法院认为,员工猝死属于非正常死亡事件,会对涉案房屋带来不利影响,由此认定房屋构成“凶宅”;而在案例2中,同为房屋内猝死事件,法院则主张人类的生老病死属于自然现象,因病发原因死亡后,不应认定房屋构成“凶宅”。笔者支持案例2中法院之主张,认为发生自然死亡或因病死亡事件的房屋不应认定为“凶宅”,因为生老病死乃人的自然规律,且不以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亦非当事人可进行选择之事项,每个人都必然经历,如将人类正常死亡亦视为“凶宅”的事由,将极大的破坏社会稳定,也会导致所有房屋均被认定为“凶宅”的风险无限放大。
(二)“边宅”的概念厘定
通过对以上案例论述分析并结合现行学说主张,所谓“凶宅”,是指与发生自杀、凶杀、意外死亡等非正常死亡事件之间存在较大联系,虽实际使用价值未受影响,但却会使一般民众产生恐惧和忌讳心理的房屋。“凶宅”极大地降低了购买者的心理预期,在交换价值及内在品质方面与普通房屋间均存在重大差异。具体表征如下:
其一,与非正常死亡事件存在较大联系;非正常死亡事件非必须发生于房屋之内,具体而言,过世之人的最终死亡地点并不要求必须发生涉诉房屋之内,只要非正常死亡事件与涉案房屋存在较大联系,进而影响包括房屋所有权人在内的一般大众对该房屋的评价,即可认定该房屋为“凶宅”,如涉案房屋发生跳楼身亡事件。
其二,“凶宅”并未影响房屋的实际使用价值。“凶宅”本身房屋并未发生实体毁损,不构成人们对房屋本身进行物质性使用的障碍,不会对房屋的区位、面积、结构、材料、基本设施、使用功能等房屋客观效用造成影响。
其三,“凶宅”影响人们对房屋的心理感受。房屋内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发生虽然对房屋结构本身不构成损害,但基于一般人对死亡的恐惧和忌讳心理,客观上会不同程度的加重居住人的心理负担,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住宅内发生的非正常死亡事件感到不同程度的恐惧并对死亡现场心存芥蒂是客观存在的心理现象。
其四,“凶宅”致使房屋流转遭受严重阻碍。源于人们对“凶宅”的忌讳、恐惧等心理,不少人不愿意居住于此,从而使得房屋无论出租或转让都增加了困难,导致房屋在后续可能的出租、出售中受到严重阻得。“凶宅”出租、转售的难和贬值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成为市场价值规律在消费文化、消费心理、消费理念上的反映和体现。
其五,“凶宅”所引发的心理影响具时限性。“一日凶宅”并不必然导致“终身凶宅”,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凶宅”忌讳、排斥、恐惧等心理感受会削弱,当距离承租人自杀事件之发生超过一定的时间,则因“凶宅”引发的消极心理影响会逐渐减弱甚至消失。“凶宅”对房屋评价产生的消极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化,但在淡化之前的一定期间内会持续存在。
2
“凶宅”贬值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
当前司法实践中,房屋所有权人针对“凶宅”损害赔偿的主张主要包含两方面责任,一方面为房屋贬值损害赔偿,另一方面为精神损害赔偿。“凶宅”贬值损失系财产损害赔偿责任纠纷,须满足财产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方得请求数济,现行立法中可作为房屋所有权人主张“凶宅”贬值损害赔偿的法条依据有《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9条、第24条;房屋所有权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法条依据为《侵权责任法》第22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以《侵权责任法》规定为中心,下文重点分析“凶宅”贬值损害赔偿的主要内容。
(一)“凶宅”贬值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
《侵权责任法》第6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19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第24条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
(二)“凶宅”贬值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
“凶宅”贬值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根据《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和我国司法实践,“凶宅”贬值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有四: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发生;“凶宅”贬值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非正常死亡事件与“凶宅”贬值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行为人的主观过错。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发生是“凶宅”认定以及展开“凶宅”贬值损害赔偿的基本前提,以上“凶宅”的界定部分已进行详细分析,此处不再赘述,主要对以下三方面要件予以明确。
其一,“凶宅”贬值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
侵权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以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为前提,由此,“凶宅”贬值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是房屋所有权人主张财产损害赔偿法律关系赖以发生的根据。财产损害事实又称为财产权利的损害,是指加害人行为侵害他人所有的财物以及其他财产权利,致使受害人的财产或者财产利益遭到损坏或毁灭的损害事实。侵权行为对财物或财产利益的损害不仅表现为就财产或财产利益发生的财产法律关系的损害,而且实际地表现为受害人拥有的财产和财产利益的价值的减少,即受害人拥有的财富的减少或损失。具体至“凶宅”贬值损害赔偿纠纷中,则要求房屋所有权人因“凶宅”贬值遭受实际损害。
其二,非正常死亡事件与“凶宅”贬值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的确定,直接决定了行为人是否要承担责任,因此判断因果关系是否成立尤为重要。在侵权责任的要件中,因果关系是指行为人的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具体至“凶宅”贬值损害赔偿纠纷中,则是指非正常死亡事件发生与房屋价值贬损之间的因果关系,具体而言,房屋价值贬损的结果是因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发生引起的,房屋价值贬损是非正常死亡事件的结果,非正常死亡事件是房屋价值贬损的原因。查找因果关系的目的不在于考虑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违法,而在于确定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联系,因果关系的确定直接决定了行为人是否要承担责任,因此非正常死亡事件与凶宅贬值损害之间因果关系的成立至关重要。
其三,行为人的主观过错。
贬值损害偿纠纷中“死者已矣”,所谓过错主要指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发生中与死亡人非正常死亡事件发生有关的第三人是否存在主观过错的问题,如与自杀人一起居住的人、非正常死亡人的继承人、房屋租赁中的第三方中介机构、房屋装修中派遣装修工人的装修公司等,只有其对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发生存在主观过错的情形下,方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行为人主观过错的认定由房屋所有权人承担举证责任。
3
“凶宅”贬值损害赔偿诉讼实证分析
从现行司法审判实践来看,房屋所有权人基于非正常死亡事件提起“凶宅”贬值损害赔偿诉讼争议焦点集中于:房屋所有权人是否遭受实际损害、非正常死亡事件与房屋价值贬损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凶宅”贬损价值的具体范围确定等方面。
(一)房屋所有权人是否实际遭受损害
《侵权责任法》规定侵权责任的承担须以发生损害为必要,且这种损失必须是客观上已经实际发生。由于“凶宅”贬值损失无形化程度较高。建立在人们对“凶宅”忌讳、恐惧、不安等抵触心理之上。针对非正常死亡事件发生是否对房屋所有权人成实际损害,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
案例1:潘某某与张某某、孔某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2015年11月19日,原告与被告钱某某、孙某某签订《房地产租赁合同》,约定原告将该处房屋出租给两被告,2016年9月17日,名叫“XX”的男子在该房屋内非正常死亡,死者XX系两被告亲友。针对原告所称的损失是否已实际发生,法院主张,按照原告的思路,其损失是这样得出的,假定系争房屋市场价为1000万,因房屋内发生自杀事件变成“凶宅”,现该房屋价值为800万,其中的200万差价即为损失。然而,原告并没有将该房屋出售,该房屋仍然处于原告控制之下,即使认可原告上述理论,这种损失也只是体现为一种主观上的可能性而已,“实际损失”根本无从谈起。
案例2:ト某诉王某某等物权保护纠纷案
2014年6月初,二被告借用原告石景山区八角中里xx号房屋,2014年12月29日,被告女儿王某某在原告房屋内跳楼自杀死亡。针对原告是否实际遭受损害,法院主张,从现实来看,房屋内发生过非正常死亡事件虽然不会对房屋的实际使用功能产生影响,但会引发人们恐惧、焦虑、忌讳等不良的心理感受,这种负面心理感受表现在房屋交易过程中,会导致购房者或租房者对房屋的评价和价值认可度降低,从而对房屋能否出租、出售以及出租、出售的价格产生较大影响。也正因如此,房地产交易惯例中,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将房屋是否发生过非正常死亡事件作为必须披露的影响交易决策的重要事项。因此,被告之女自涉案房屋跳楼死亡事件,导致房屋在后续可能的出租、出售中受到不利影响,原告对房屋的收益处分权能受到限制,由此导致的房屋贬值损失客观存在。
根据一般交易习惯,“凶宅”虽不构成人们对房屋本身进行物质性使用的障碍,但很难被人轻易接受,且会造成房屋正常流通受阻以及房屋价值贬损的后果。且一旦发生非正常死亡事件,无论房屋所有权人抑或房屋的潜在购买者、租赁者,均会产生对“凶宅”的消极心理评价,且任何一方无法将房屋恢复至非正常死亡事件发生之前人们对房屋的评价状态,发生非正常死亡事件的房屋在房屋交易市场上已然产生价值损耗,而无论其出售、租赁与否,房屋价值损耗均客观存在,对房屋所有权人形成客观财产损害,正如在里德诉金案( Reed V.King)的上诉案中,加州法院强调,原告提出的索赔并非基于她居住在这所房子里的恐惧或不适,而是基于这一邪恶事件导致的财产贬值这一客观事实。此外,近年来,我国现行司法实践中因房屋“凶宅”性质所引发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支持合同撤销、合同解除的判决,亦从侧面对“凶宅”的价值贬损客观存在提供有力支撑。
(二)非正常死亡事件发生与“凶宅”贬值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
“凶宅”贬值损失系财产损害赔偿责任纠纷,须满足财产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方得请求救济,其中非正常死亡事件发生与房屋贬值之间的因果关系无疑是构成要件的核心。作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之一的因果关系,是审理“凶宅”贬值赔偿案件时法官无法绕开的问题。
案例1:ト某诉王某某等物权保护纠纷案
针对非正常死亡事件与“凶宅”贬值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方面,法院认为,根据社会常识和交易习惯,普通人在购房时,通常会综合考察房屋的地理位置、建设信息、周边设施及房屋价格等作为最后审慎决定购买的因素。房屋交易价格的高低,一般主要取决于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调整和房屋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对于发生非正常死亡事件的房屋,购买者是否存在避讳心理及其程度会因人而异,对房屋评价和价值认可的程度也会受事发时间的长短、不幸事件的不同程度、购买者文化水平、社会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由此导致房屋贬值程度也不尽相同。因此,房屋内发生非正常死亡事件只是可能导致房屋交易价格受影响因素之一,与当事人实际交易价格之间并不存在对等的直接因果关系。
案例2:潘某某与张某某、孔某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法院主张,一般情况下,判断因果关系应从加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必然性、自然导致等方面来分析,通常援引如下方法:“大前提:依据一般的社会智识经验,这种行为能够引起该种损害后果,小前提:现实中该种行为确实引起了该种损害后果,结论:两者存在因果关系。从大前提上看,并非所有人会对房屋的居住产生忌讳,其自杀行为也不一定能够导致房屋贬值。从小前提上看,本案中原告并未将该房屋实际出售,这种所谓的“损害后果”只是一种主观可能性,并未实际发生,不符合该小前提的要求。故从因果关系的两个组成部分来看,原告所称的房屋贬值损失与被告的行为及XX自杀行为间并不存在侵权法要件中的因果关系。
通过以上案例可以看出,虽然法院认可“凶宅”贬值损害事实存在,但普遍以房屋价值受多方因素影响,非正常死亡事件之发生不必然导致房屋价值贬损为由否认非正常死亡事件与“凶宅”贬值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案例1中,法院主张房屋交易价格取决于市场经济价值规律和房屋本身固有价值,由此否认因果关系的存在;在案例2中,法院以并非所有人对房屋居住产生忌讳为由,认定非正常死亡事件不必然导致房屋价值贬损。
笔者认为: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发生,虽然并未造成涉案房屋外观形体之毁损或功能减损,然而依社会通常观念和事物发展进程,人们对曾经发生过非正常死亡事件的房屋普遍存在忌讳或恐惧心理,这又客观上导致涉案房屋交换价值的下降或出租收益之降低,此外,会造成房屋流通上的长期障碍,相当长的时间内房屋处于空置状态,造成涉案房屋遭受价值贬损,符合相当性因果关系的要求。
(三)“凶宅”贬损价值的具体范围确定
《侵权责任法》第19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这是对财产权受侵害时承担赔偿损失责任的损失额计算方法的规定。“凶宅”所导致的房屋价值损害的量化和计算,是房屋所有权人获取“凶宅”贬值损害赔偿的先决条件。司法实践中,法院普遍以房屋所有权人未能举证证明房屋贬值损失的责任范围为由,驳回“凶宅”贬值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
案例1:程某某、王某某等与东莞市唐庭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针对“凶宅”贬损价值的具体确定,本案诉讼过程中原告申请对案涉房屋因装修工人死亡引起的市场价值贬损金额进行鉴定,法院予以准许,并摇珠委托东莞市广协鉴定评估有限公司进行鉴定;后该鉴定机构出具情况说明,称由于案涉当事人认为房屋价值贬损原因是因装修工人现场死亡造成的,此类型业务带有封建迷信色彩,不是其鉴定评估业务范围,无法对本案的贬损金额作出价值评估。
案例2:刘某某与张某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上诉案
本案中,原告刘某某主张宅院因张某某的死亡成为“凶宅”影响房屋后续出租,张某应依公序良俗,按照为期五年,每年三万元的标准各自承担一半的责任,用于赔偿其无法正常出租涉诉宅院的损失,法院以该主张缺乏明确法律依据为由,判决不予支持。
案例3:潘某某与张某某、孔某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本案中原告为证明房屋因“凶宅”所引发的贬损价值范围,提供了关于房屋市场价格的数份电话咨询录音作为证据,在电话录音中,所谓的中介工作人员提到“这样的房屋可能要贬值20%到30%……”以此作为“凶宅”贬损价值的依据。法院主张原告虽提供了与房产中介人员的三段电话录音,但无法确定这三段录音是否来自与房产中介人员的谈话。即使认可这些电话录音,但从电话录音的内容也可以看出,中介人员对于房屋贬值情况并非绝对肯定,例如,有的中介人员提到,“对于这样的房屋,买家是不是介意要看各人的,有的介意,也有的不介意”,“跌价多少也不确定……”由此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也难以满足充分、完整的要求。
通过以上三个案例可见,当前司法审判中针对“凶宅”贬损价值的计算缺少统一标准,计算方式混乱等问题,房屋所有权人举证“凶宅”具体贬损价值的途径有四:其一,委托专业机构评估,如案例1中,委托具备资产评估资质的专业评估机构通过符合法律规定的评估程序对房屋市场价值以及市场价值降低的情况予以评估,然由于“凶宅”贬值损失无形化程度较高,建立在人们对“凶宅”忌讳、恐惧、不安等抵触心理之上,鉴定机构无法对“凶宅”价值贬损金额作出价值评估;其二,租金计算法,如案例2中,房屋所有权人主张以租金乘以5年计算贬值损失;其三,差额计算法,如案例3中,房屋所有权人以出售房屋的实际价格与市价之间差额主张贬值损害赔偿的范围;其四,依交易惯例计算,如案例3中,房屋所有权人亦主张通过房屋交易市场上针对“凶宅”价值贬损的交易惯例确定贬值损害的具体金额,但证据的证明力及证明要求等均受到法院的否定性评价。
笔者认为,虽然当前针对“凶宅”贬损价值的范围确定缺乏明确具体的评判标准,但法院不应因此而全面否定房屋所有权人“凶宅”价值贬损的损害赔偿请求,“凶宅”贬损价值范围的确定是确定房屋贬值损失赔偿数额的依据,而非获得损害赔偿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当事人已经证明其房屋受有损害而无法证明具体损害数额情形下,法院应综合具体情形推定房屋贬值损失的发生、酌定“凶宅”贬损价值的具体范围。如在案例1中,鉴于房屋所有权人未能提供有力证据证实其财产损失金额,鉴定机构对此也无法评估,法院综合考虑原告购买房屋时的价格、房屋受损时的市场价格、被告的过错程度等因素,酌定被告赔偿原告共计50000元,该种做法值得称赞。在法院酌定“凶宅”具体贬损价值的范围方面,建议可采取收益平均法加以确定,即根据非正常死亡事件发生前的一段时间房屋所有权人的平均收益(如租金)确定可得利益损失,如果采用平均收益法无法确定可得利益损失,也可以采取同类比照法加以确定,即以同时期、同户型、同位置、同等条件房屋的所有权人的平均收益确定可得利益损失。此外,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构建“凶宅”备案数据库,并设定“凶宅”价格评估的客观标准。
4
小结
住宅吉样与安宁是我国普遍存在的民俗文化心理,是与中华民族历史传统相连结的特有价值观念和取向。“凶宅”价值贬损的根源在于交易市场对发生“非正常死亡事件”房屋的消极评价,这种消极的评价直接转化为交易市场上“凶宅”交易价格的下降,最终体现为房屋所有权人财产权益受损。因此,“凶宅”的价值贬损是一种客观财产损失,并且满足相当性因果关系要求,应当予以赔偿。在赔偿范围的具体确定方面,建议构建全国凶宅备份数据,并设定凶宅评估的客观标准,根据公平原则和利益衡量原则,合理确定房屋价值贬损的具体数额。通过对“凶宅”贬值损害赔偿法律适用的探讨。以进一步缓解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解决“凶宅”贬值损害赔偿纠纷的压力、保护房屋所有权人财产权益的同时,有助于促进房屋交易市场的稳定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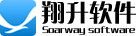


 行业资讯
行业资讯
 联系电话:059187640886 / 059188968588
联系电话:059187640886 / 059188968588 企点客服QQ:800054909
企点客服QQ:800054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