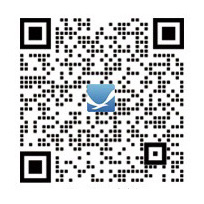❖ 广州案例 ● 第五十九期
随着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日常往来越来越频繁,两地居民之间的跨境婚姻数量呈逐年攀升,法律争议也随之增加。
涉港婚姻中,夫妻在婚内购置并登记在个人名下的内地房产,是否为夫妻共同财产?法官审理过程中究竟是适用内地法律还是香港法律?请大家一起走进今天的广州案例。
案例一
1基本案情
丈夫张某与妻子吴某均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其二人于1968年5月在香港结婚。
1992年3月14日,吴某与谢某签订《协议》,约定由吴某、余某元向谢某共同购买位于广州地区的案涉房屋,其中案涉房屋地下、二楼、四楼及三楼以上楼梯位和以后房屋上空之发展权归吴某所有,三楼归余某元所有。同年3月16日,谢某与吴某、余某元签订《广州市房屋买卖合同》,对案涉房屋的面积、出售价格等进行约定。后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就案涉房屋首层、2、4楼向吴某核发房产证,共有情况记载为“单独所有”。
2005年12月10日,吴某与张某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域法院出具《离婚令》解除婚姻关系。
2016年2月24日,吴某作为卖方,与陈某、中介公司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将案涉房屋首层、2楼、4楼以17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陈某。3月2日,案涉房屋登记到陈某名下。
同年8月3日,张某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称案涉房屋是其与吴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张某主张吴某与陈某恶意串通、低价交易,损害了其作为房屋原共有人的利益,故向法院请求确认吴某和陈某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
2争议焦点
张某是否为案涉房屋的共有权人?
3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房屋是张某和吴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应属于张某和吴某的夫妻共同财产,而二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域法院颁布的离婚令中并未对案涉房屋进行处理。同时,法院通过分析认定陈某非善意购买人,故判决确认吴某和陈某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
➣广州中院认为:首先,张某、吴某均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应参照涉外案件进行审理。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由于案涉房屋位于我国内地,该房屋所有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等应适用我国内地法律。本案中,案涉房屋一直登记在吴某名下并由其个人所有,张某并未登记为产权人,因此张某不可能依照我国《物权法》的规定成为案涉房屋所有人。从张某在本案的主张来看,张某是以吴某前夫的身份主张案涉房屋是其与吴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因此案涉房屋是否系吴某与张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是本案的先决问题。由于张某与吴某均系香港居民,两人在香港结婚并离婚,关于张某与吴某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问题,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四条规定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处理。一审法院适用内地法院认定张某与吴某的夫妻财产关系,属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对此予以纠正。根据香港法例第182章《已婚者地位条例》的相关规定,张某关于案涉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的主张不能成立。由于张某并非案涉房屋共有权人,并非本案适格原告,广州中院裁定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张某的起诉。
案例二
1基本案情
何某(男)与刘某(女)系夫妻,何某系香港居民,刘某系内地居民。双方于1999年在内地登记结婚,婚姻至今仍在存续期间。案涉房屋的登记权属人为何某,占有份额为全部,发证日期为2006年12月20日。
2016年10月28日,何某与张某、房地产中介公司三方签署《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何某出售案涉房屋给张某。
之后,张某多次联系何某办理过户手续均无果,张某遂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何某协助办理过户手续。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刘某以涉案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何某无权处分为由,申请参加诉讼,请求判令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
2争议焦点
刘某是否为案涉房屋的共有权人?
3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张某与何某、房地产中介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主体适格,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是为有效,对合同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均应遵照履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张某已按合同约定向何某支付了定金,并已获得银行对其贷款申请的审核通过;何某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协助办理房屋转移过户登记手续,已经构成违约。故一审法院判决何某协助张某将案涉房屋转移登记手续。
➣二审法院认为:由于何某系香港居民,故本案应参照涉外民商事案件进行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因案涉房屋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故本案应适用内地法律作为处理物权纠纷的准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夫妻财产关系,当事人可以协商选择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共同经常居住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住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虽然何某与刘某没有选择适用的法律,但双方婚姻缔结地在内地,双方共同经常居住地在内地,故应当适用内地法律作为处理何某与刘某之间夫妻财产关系的准据法。由于案涉房屋的取得是发生在何某与刘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故根据我国婚姻法规定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本案中,何某擅自处分其与刘某的共有房屋,至今未得到刘某的同意及追认,在此情况下,张某要求何某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手续,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二审法院改判驳回张某的上述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随着中国内地居民与香港居民之间的日常往来越来越频繁,两地居民之间的跨境婚姻数量呈上升趋势。而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不断推进以及湾区内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紧密,可以预见涉及到跨境婚姻的法律争议也会随之增加。上述两个案件就是由于香港与内地的夫妻财产制度的不同认定,导致了不同的裁判结果。
在上述两个案件中,都涉及到一个先决问题,那就是香港居民在婚内购置并登记在个人名下的内地房产,是否为夫妻共同财产。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法律适用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四条,“夫妻财产关系,当事人可以协商选择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共同经常居住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住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
对于该条法律规定,应分三个层次予以理解:首先,在涉外的夫妻财产关系中,当事人可以协商选择适用的法律,但并非不考虑连接点进行任意选择,而是应在经常居住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进行协商选择;其次,如当事人并未对适用法律予以协商选择,则应适用当事人共同的经常居住地法律;最后,如当事人没有共同的经常居住地,则应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规定,涉及香港、澳门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上述法律规定。
在案件一中,张某与吴某均系香港居民,且二人的结婚登记地以及离婚地均在香港,并无证据证明二人曾协商选择适用内地法律处理夫妻财产关系,双方也确认未在内地共同居住过。因此,经办法官对于二人夫妻财产关系适用了香港法进行处理。
在香港,按照《已婚者地位条例》相关规定,夫妻之间实行分别财产制,男女婚后拥有相同的对自己婚前和婚后财产所有权的能力和承担债务的能力,即夫妻双方婚前和婚后所得财产男女归各自所有,并单独行使管理权、收益权和处分权,但也不排斥妻以契约形式将财产的管理权交给丈夫或双方拥有一部分共同财产。
综上,在案件一中,经办法官根据香港《已婚者地位条例》的相关规定,在无证据证明吴某和张某约定案涉房屋属于共同财产的情况下,认定案涉房屋属于吴某的个人财产,并对张某关于案涉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的主张予以驳回。
在案件二中,虽然何某系香港居民,但经查明其与刘某的经常居住地在内地,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应适用共同居住地法律,即内地法律。根据我国《婚姻法》第十七、十八、十九条规定,我国实行约定财产制和法定财产制相结合的财产制度。约定财产制的效力优先于法定财产制。我国的法定夫妻财产制是婚后所得共同制。婚前财产归个人,婚后所得财产如果没有约定,则为夫妻共同财产。因此,在无证据证明何某与刘某之间约定财产分别制的情况下,根据《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案涉房屋应该属于何某和刘某的夫妻共同财产,何某的处分行为未经刘某同意,属于无权处分。综上,二审也作出相应的调整。
法官提醒
买卖房屋是人生大事,在进行房屋买卖交易前应对房屋的各个方面都给予充分的了解,特别是对出卖方的婚姻状况以及双方对于婚内财产的处分约定。在必要时应当要求出卖方出示相应的证明,以确保其处分行为是有效的。如案例二中的情况,如中介机构在交易前能对出卖方的婚姻状况进行相应的审查,也许就能避免此次交易失败的风险,买房人也不会遭受损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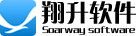


 行业资讯
行业资讯
 联系电话:059187640886 / 059188968588
联系电话:059187640886 / 059188968588 企点客服QQ:800054909
企点客服QQ:800054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