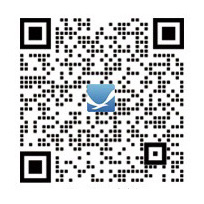不动产登记制度对物权的确认不具有绝对化效力,登记资料的证明力也要考虑到各类约定的或法定的证据抗辩权问题
不动产登记资料虽然属于法定书证的范畴,具有较高的证据效力,但其证明力并不能绝对化,要考虑到各类约定的或法定的证据抗辩权问题。同时,不动产登记制度对物权的确认亦不具有绝对化效力。
不动产登记效力的抗辩权问题。第一是不能以某项不动产未经物权登记而反向制约对该不动产实施民事法律处分行为的效力。因为《物权法》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
第二是基于意思表示不真实、恶意串通或通谋虚伪表示所产生的登记资料,其证明力存在被撤销或被否决的法律风险。
第三是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物权效力。此时,即便尚未办理不动产登记亦不能否定不动产物权的发生或消灭效力。
第四是依据《物权法》第28条,依法律文书或征收决定等已经享有物权的主体,如果对第三方再次实施物权处分,则依照法律规定应首先办理变更登记,否则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
第五是主张构成善意取得且已完成物权登记的,如该类行为涉及违反《合同法》第52条规定,或因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法定事由被撤销或被确认无效的,则即便对已完成登记行为亦不得认定其构成善意取得。
第六是不得将不动产登记簿与不动产权证书的证明力绝对化。长期以来,不动产登记实务领域及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个重大误解,即将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效力绝对化,似乎物权人只有将不动产记载于登记簿后才享有物权,或者记载为何种权利状态就享有何种物权,否则就不享有物权或仅享有有限的物权。
但事实上,上述观点本身存在循环论证的错误。其成立的前提是假定登记簿对不动产权利的记载处于完全准确且周全的状态,但又不能绝对肯定登记的记载达到了前述要求。如此,当登记簿的记载出现瑕疵时,即无法用登记簿自身的登记内容来确认登记的正确性。显然,应以物权的原因行为来记载及修正物权登记簿的登记状态。
第七是共有物权法律关系中,不因未履行共有权登记而否定物权的共有属性。根据不动产登记规则,不动产登记机构可向全体共有人合并或分别发放不动产权证书,并注明共有情况和列明全体共有人。
司法实践中,确定共有物权法律关系并不绝对依赖于是否办理了共有权登记。尤其在家庭共有权制度下,并非只有记载于该不动产权证书之中的家庭成员才享有物权。相反,只要是具备家庭共有财产权适格主体的家庭成员,即便未被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或不动产权证书之中,其依然享有共有物权。
不动产物权登记资料的证明力问题。一是不动产权属证书与证明文件。应正确认知这两类书证的证明力。这两类书证虽然均具有不动产权利的表征作用,但对其各自的适用功能并不能混为一谈。登记证明主要适用于办理抵押权登记(如他项权利证书)、地役权登记、预告登记、异议登记等具有阶段性和程序性意义的不动产权益登记事项。除此之外,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依法向权利人核发不动产权证书。核发该两项书证的主要依据是不动产登记簿,但如果登记簿信息存在错误的,则相关不动产权证书和权利证明文件均将失去存续的基础,存在被提出异议、被更正或被撤销的法律风险。
二是因换发、补发不动产权证书或证明文件所形成的书证资料。此类法律文件遭到污损、破损的,可以申请换发;遗失、灭失的,可以申请补发,并由不动产登记机构在其门户网站上刊发不动产权利人的遗失、灭失声明15个工作日后予以补发。前述补发信息须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并在不动产权证书或者不动产登记证明上注明“补发”字样。
三是因不动产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行使更正登记权、异议登记权、预告登记权等形成的登记资料。无论是更正登记还是异议登记,其核心资料是证实登记确有错误的材料,也包括具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必要材料。预告登记中的核心资料则是预告登记依托的基础法律关系文件及载明当事人关于预告登记约定的资料。
四是基于《物权法》第28条授权而产生的不动产权属登记资料。包括不动产行政裁决文书、司法裁判文书、调解书和仲裁裁决文书等,当事人可以持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生效决定书单方申请不动产登记。
五是基于人民法院等的协助执行法律文书所产生的登记资料。包括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书、保全裁定书、拍卖成交裁定书、以物抵债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等所形成的处分不动产权利的法律文件。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对人民法院的司法协助执行行为,对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的协助查封行为,对人民政府因征收或者收回不动产的决定而要求的注销登记行为等,不承担实体审查义务而应当直接办理相关登记。
六是法律、行政法规或规章规定的其他登记职责所产生的登记资料。
应当完善登记类证据资料的查询与调取制度。
原国土资源部于2018年3月2日发布《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对登记资料查询制度进行了完善。但目前律师调查取证权仍受到诸多限制,有待进一步调整。
根据《律师法》的授权,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同时规定,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
据此,律师调取不动产登记资料并没有任何法定的限制性规定。因此笔者认为《办法》将律师申请查询内容除包含当事人可查询范围外,仅被限制在三类列举性范围内,有所不当。
此外,目前的规定将不动产“利害关系人”的范畴限制为“因不动产存在相关民事纠纷且已经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的主体,并且以“提交受理案件通知书、仲裁受理通知书”为查询前置条件。相应地,将律师的取证权亦限制在“诉后”调查,忽视了律师的“诉前”调查取证权。
《办法》对律师持法院“调查令”进行查询的权利性质未能明确认知。此类调查中,律师系受人民法院授权代行司法调查权。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因此,在律师持调查令的情形下,登记机构对调查令所列示的调查范围不应进行限制。
因此,无论涉及国家秘密或是商业秘密的登记资料,律师和法官只是负有保密义务,并不应就此在取证时间段及内容方面限制或剥夺其调查权或案情知悉权,这正是《办法》之立法思维中应当继续完善的重要内容。
【来源】《中国不动产》2018年第9期
【作者】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师安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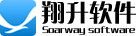


 行业资讯
行业资讯
 联系电话:059187640886 / 059188968588
联系电话:059187640886 / 059188968588 企点客服QQ:800054909
企点客服QQ:800054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