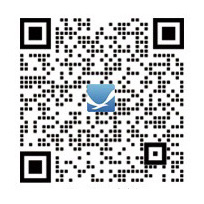“半城镇化”的分歧
在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一直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主张发展特大型城市,不应该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另一种是限制特大型城市的发展,平衡发展中小型城市,所以城市化在他们看来是“城镇化”。
持第一种观点最有代表性的,应该要数上海交通大学的陆铭教授。
在《大国大城》一书中,陆铭教授有几个非常典型的判断,比如行政手段不能控制特大型城市的人口增长,以人口规模来看,上海还太小了。他认为,首位城市的人口规模是由国家总人口规模决定的,比如纽约、东京、首尔、伦敦、巴黎等城市,其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都比上海要大,纽约市人口占美国的2.7%,伦敦人口占英国的13.1%,东京都的人口占日本人口的10.3%,如果算东京圈,它的人口达到了3600万,占日本人口比例达到了28.4%;法国的人口同样绝大多数集中在巴黎,达到了15.9%。一些小国,比如韩国、奥地利、秘鲁等,其首都人口都超过了20%。因此,从国际经验来看,控制特大城市的规模既不科学,也不经济,中国特大城市的人口继续增长,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陆铭教授的某些观点也让很多人难以接受,比如他说空心村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只需留下少数村落。
与陆铭教授相对的,是另一种所谓的“均衡派”,主张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展,限制特大城市的规模,他们将如今的城市病归因于城市规模的快速膨胀和人口数量的增加。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就是限制特大城市规模的中坚力量。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始终实行的都是限制大城市发展的战略。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7.9%。人口超过500万的大城市,只有三个直辖市,人口超过千万的大城市更是一个都没有,人口都被户籍牢牢地栓在了农村和中小城市。即使是今天,虽然人口的流动自由了,但户籍仍被限制,别看今天有所谓的“抢人大战”,但其门槛,对今天超过2.3亿的农民工来说,仍是巨大的天堑。
近些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以上两种思路的碰撞也越来越激烈,比如今天被很多人关注的“半城镇化”现象,就成了两种思路互相攻击的口子。所谓半城镇化,指的是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过程中的一种不完整状态。他们职业是工人,身份是农民;活在城市里,死要回乡下;在城里工作,却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许多方面并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在城市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未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这部分“灰色人口”的解决,到底应该用什么方式?是放开人口流动的限制,还是均衡发展城市,让他们回到自己家乡就能就业呢?
某种程度上看,今天都市圈的概念,很好地弥合了这种分歧。
“都市圈元年”
在学界看来,2019年应该是中国的“都市圈元年”。有几个重要的节点,2月18日,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重点打造大湾区都市圈,“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京津冀”、“长三角城市群”、“上海大都市圈”之后又一个“超级都市圈”成形。2月21日,国家发改委在官网公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这意味着,中国城镇化全面进入了“都市圈时代”。
都市圈的发展,既突出内部的强核城市,又强调内部的协同发展。清华大学中国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尹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发展现代化都市圈“意味着中国从一个单打独斗的城市竞争时代进入了一个区域协同和区域合作的时代”, 中国城市化进程还远未到收官阶段,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聚集仍然是个大趋势。如何避免以前“摊大饼式”的战术性错误,培育发展都市圈,从单一核心板块的中心城市走向区域协同式的发展是一剂良方。
如今,陆铭教授认为,这剂“良方”的各种药引已经配齐。在他与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冯奎合作的一篇文章中,他们提出了四条依据:
一是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将近60%,进入城市型社会。美国、日本以及欧洲一些国家都市圈发展的经验表明,城镇化率30%时,城镇化开始出现加速度,中心城市壮大。城镇化率超过50%以后,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功能显著增强,核心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开始加速形成都市圈。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中国的一些中心城市、省会城市已经开始了都市圈发展战略。数据显示,到2017年底,长江三角洲、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分别以2.2%、0.6%和2.3%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国19.2%、12.4%、9.7%的经济总量和11%、5%和8%的人口,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二是核心大城市已经足够强。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与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共同发布《2018年中国城市圈的发展研究报告》显示,都市圈划定的基本门槛是,中心城区人口规模500万人以上,而且在1小时通勤圈内,人口密度超过1500人/平方公里。按照上述标准,除港澳台地区之外,报告在全国识别出34个都市圈。
陆铭教授给出一组数据,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规划司参与的一项研究报告,按照GDP规模,中国排名前30位的城市的GDP全国占比达到42.5%;按主板上市企业数量,排名前30位城市的全国占比高达69.7%,其中排名前三位城市的全国占比达39.6%;按照制造业辐射力,排名前30位城市的货物出口全国占比高达74.9%;按机场便利性,排名前30位城市的旅客吞吐量高达81.3%;按集装箱港口便利性,排名前30位城市的集装箱吞吐量高达97.8%;按高等教育辐射力,排名前30位城市的211、985大学数量全国占比高达92.8%;按医疗辐射力,排名前30位城市的三甲医院数量全国占比约为50.2%。未来以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为引领,其他30-50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构造已初具雏形。
三是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较为充分的成长。这主要集中在江浙沪闽粤等经济发达省份,都市圈既需要核心城市的引领,也需要高质量的中小城市“众星捧月”,而长三角、珠三角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数目多、质量高,有利于充实都市圈的内容,如果以经济总量和居住人口来评估,长三角、珠三角的一些乡镇甚至都能超过内地的地级市,因此一批特大镇、特色镇的成长,为未来都市圈发展也创造了条件。
四是高速公路和高铁通勤发展迅速。这也是打通都市圈的关键条件,而轨道交通、快速路、高速路等的完善,让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以及轨道上的其他都市圈正在加紧形成,半小时通勤圈、1小时交通圈的提速,将为中国都市圈大发展创造条件。
都市圈元年的到来,让我们看到了解决“半城镇化”的曙光。
新的均衡
某种程度上说,都市圈的发展,是今天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大城派”与“均衡派”找到的最好的共识。在当前户籍制度仍未松绑的情况下,完全放开特大城市的发展并不容易,但可以打造区域中心,在区域内部进行改革与协同;同样,如果不解决“半城镇化”的问题,企图用行政力量来均衡城市的发展也不现实。
而共识就来源于都市圈的发展,能够一定程度上解决区域间发展失衡的问题。“失衡”,是城市化的基本形态,也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出现的现象,这也是陆铭教授坚持认为空心村的出现将是必然现象的原因。我们很难追求绝对的均衡,只能通过“城市圈”的培养,实现大致的均衡。因此,在《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的解读中,国家发改委反复强调“因地制宜推进都市圈建设”,做好推动统一市场建设、基础设施一体高效、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产业专业化分工协作、生态环境共保共治、城乡融合发展等。
按照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城市群与都市圈研究分中心主任卢庆强的看法,都市圈的发展,将填补城镇化战略的最后一块版图,而未来中国将形成“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大小城市协同发展—特色小镇—乡村振兴”的战略格局和全尺度的空间组合链条。
这就是尊重城市发展规律与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了。城市发展的规律,用陆铭教授的话说是:
第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城市化水平越高。
第二,城市人口的分布,不管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趋势都是人口从小城市向大城市集中。
第三,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几乎无一例外的人口在重新向市中心集中。
而中国的特殊国情,一是中国人有安土重迁的文化,不太可能轻易放弃故乡(农村)。二是在全面小康、精准扶贫的方针之下,城市和农村的发展都应该并重。
因此,在这种都市圈战略的规划下,中心城市能成为圈内的核心,解决首位度城市发展问题,即使全国的户籍政策仍有屏障,但在圈内的协同中也能解决人口的自由流动,破解“半城镇化”难题。在这个城市圈内,有一个或多个中心城市,是区域的经济文化中心,他们对周边人口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也能部分缓解特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再加上围绕着中心城市的特色小镇、乡村振兴策略,通过产业,而非简单的政策推动内部人口的自由流动将成为新的平衡点。近年来,国家陆续把成都、西安、郑州、武汉等9个城市列为国家中心城市,就是在“失衡”中寻找“新的均衡”。
一直以来,人们调侃“一线城市容不下肉身,三四线容不下灵魂”,都市圈的发展,特别是通勤条件的改善,身体在三四线,灵魂栖息于一线城市,也不是不可能。
都市圈能解决城市病吗?
都市圈的发展,给予社会最大的期待之一,应该是解决城市病了。
中国的城市,正在出现的城市病主要有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和犯罪三个方面。从中国城市发展的历程来看,无论是纵向对比,还是区域间的横向对比,都容易轻易下结论,认为人口数量多是导致城市病的原因,认为人口持续流向北京、上海,推高了当地房地产价格,造成了北上等城市自然资源、公共资源的缺乏、同时还带来严重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因此在这种观点支撑下,2017年公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明确指出,北京城市人口规模2020年将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
但这个问题如果放到全世界来看,当我们拉长时间轴,审视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时,这个结论就会很容易被质疑。比如发达国家环境最恶化的时候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伦敦烟雾事件、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都发生于这一时期,但如今伦敦、洛杉矶的人口并未减少,反而环境更好了,其他城市,纽约、波士顿、东京、巴黎的人口也一直在增加。人口的增加,并非城市病的最主要原因,因此解决城市病的决定不是简单控制人口。
陆铭教授认为,人口的自由流动不是导致大城市出现城市病的主要原因,问题出在了规划、技术和管理上,因此,破解城市病,也应该是提供更有效的规划、技术和管理。
至少在规划上,都市圈的发展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市病。以交通为例,比如地铁面临拥堵时,是应该减少人口还是造更多的地铁,提供更加便捷的通勤条件。如果有一天,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可以实现任意地点,500米范围内必有地铁站,地铁出行比例达到80%以上,即使政府官员和企业高管也乘地铁上班,那么可以想象,那时的地面交通将不会再拥堵。而这就是纽约,东京,香港已经实现的景象。数据显示,在轨道交通、 公共(电) 汽车、小汽车、出租车四种主要出行方式中,东京圈轨道交通出行比例为59.6%,东京都区更是高达78.4%,而在北京这一比例仅为22.7%。原因在于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较短,路网密度明显较低。
还有一份数据,可能更能说明问题。高德地图发布的《2018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显示,济南、呼和浩特、贵阳的常住人口规模不足1000万,哈尔滨常住人口为1092万,但这些城市的拥堵指数却高于上海、广州、深圳。
此外,都市圈内的综合改革,社会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也能缓解城市病。比如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提出“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在具备条件的都市圈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积互认”,在都市圈内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一体化和均等化的进程中,逐步调整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数量、结构和布局来适应人口增长带来的有效需求,也是缓解城市病的重要方法。
最后一点,是都市圈内部的产业带动能力。人口的流动都是随着产业走的,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城镇化规划处处长韩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都市圈是解决大城市病的有效途径,将中心城市非核心功能疏解到周边中小城市,有效缓解交通拥堵、房价高企等问题,推动解决大城市病。”都市圈通过基础设施连接以及公共服务的一体化,把更多机会通过市场的方式让渡给城市群内富有发展活力的的其他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带动城市群的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最简单的一点,人口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向经济更发达、收入水平更高、能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地区流动,是大势所趋。如果交通、教育、医疗、政府服务等配套齐全,生活在城郊一样很方便。届时,城市将呈现“多中心化”的发展形态,人口承载能力、人才吸引力也会更强。
当然,都市圈的协调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行政力量的干预,既有统一规划的好处,但也要克服内部因为政绩考核等带来的资源抢夺。
李铁担心的是,公共服务供给的区域封闭、GDP政绩和财政供给,都以行政区为界限。行政区域之间的竞争,直接影响到基础设施区域间的配置,影响人口的流向,最终关系到利益分配格局。而由行政权力传导形成的要素积累,使中心城市产生了一定排他性。比如说,公共服务优质化、基础设施供给现代化、对低学历人口排斥、利用等级化的权力,对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强化发展约束等。
陆铭教授也认为,核心大城市迈向都市圈是全球的普遍规律,核心的问题是跨地区的资源配置受到了城市和城市之间,甚至省和省之间行政边界的阻碍。
最后还是要感叹,都市圈的发展,今年是元年,万里征程今伊始。
(来源:秦朔朋友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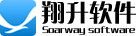


 行业资讯
行业资讯
 联系电话:059187640886 / 059188968588
联系电话:059187640886 / 059188968588 企点客服QQ:800054909
企点客服QQ:800054909